目录
快速导航-
专题:出版人才培养 | 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视域下的出版专业博士高质量培养
专题:出版人才培养 | 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视域下的出版专业博士高质量培养
-
专题:出版人才培养 | 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国际出版人才培养析论
专题:出版人才培养 | 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国际出版人才培养析论
-
专题:出版人才培养 | 出版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
专题:出版人才培养 | 出版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
-
本刊特稿 | 对话卡斯特:我们正处于传播革命的中心
本刊特稿 | 对话卡斯特:我们正处于传播革命的中心
-

理论前沿 | 分布式网络:共通体何以可能
理论前沿 | 分布式网络:共通体何以可能
-

理论前沿 | 技术的“秩序”:智能算法的分类逻辑与“共性化取代”
理论前沿 | 技术的“秩序”:智能算法的分类逻辑与“共性化取代”
-

出版史研究 | 革命记忆与舆论建构:作为话题的清末书商徐敬吾
出版史研究 | 革命记忆与舆论建构:作为话题的清末书商徐敬吾
-

学术争鸣 | 复归传播本源,重建华夏传播:对华夏传播研究两种进路及观念的存在论反思
学术争鸣 | 复归传播本源,重建华夏传播:对华夏传播研究两种进路及观念的存在论反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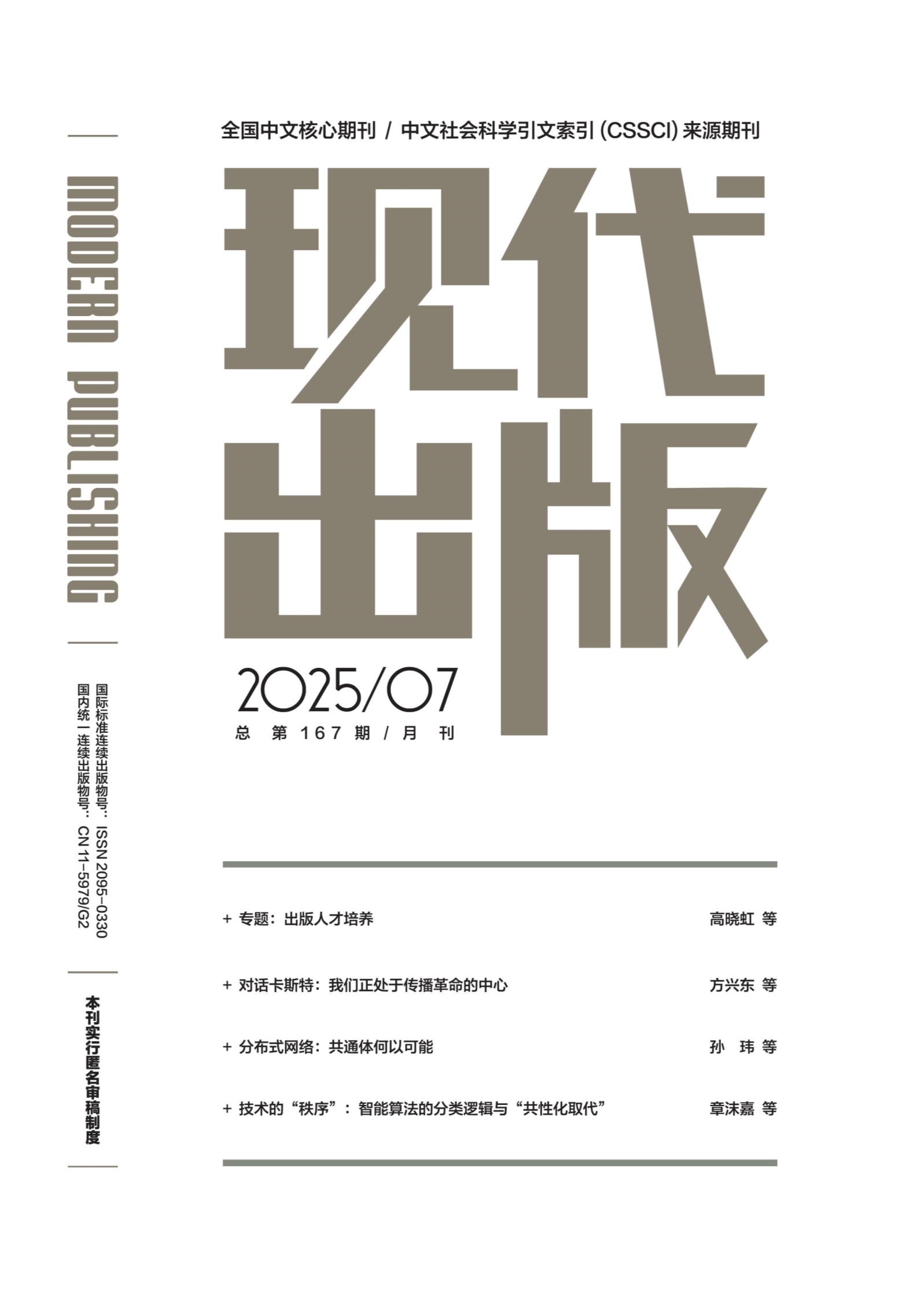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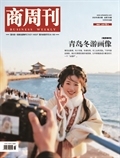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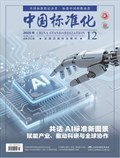

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