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录
快速导航-
东亚文明研究 | 日本分割朝鲜半岛的历史尝试
东亚文明研究 | 日本分割朝鲜半岛的历史尝试
-
东亚文明研究 | “夷”与日本华夷秩序演变
东亚文明研究 | “夷”与日本华夷秩序演变
-
东亚文明研究 | 从童子军到军国主义侵略工具:日本少年团的成立及其嬗变
东亚文明研究 | 从童子军到军国主义侵略工具:日本少年团的成立及其嬗变
-
欧美文明研究 | “幽灵统治”:英国普通法令状制度及其法律遗产
欧美文明研究 | “幽灵统治”:英国普通法令状制度及其法律遗产
-

欧美文明研究 | 美国波多马克河水污染治理模式的历史演进及其意义
欧美文明研究 | 美国波多马克河水污染治理模式的历史演进及其意义
-
古典文明研究 | 塔西佗《阿格利可拉传》中的中心与边缘
古典文明研究 | 塔西佗《阿格利可拉传》中的中心与边缘
-

古典文明研究 | “衬托者”与“附庸人”:历史书写与现实生活中的约瑟福斯
古典文明研究 | “衬托者”与“附庸人”:历史书写与现实生活中的约瑟福斯
-

丝路古今研究 | 试析“条约”与“朝贡”在缅甸的碰撞
丝路古今研究 | 试析“条约”与“朝贡”在缅甸的碰撞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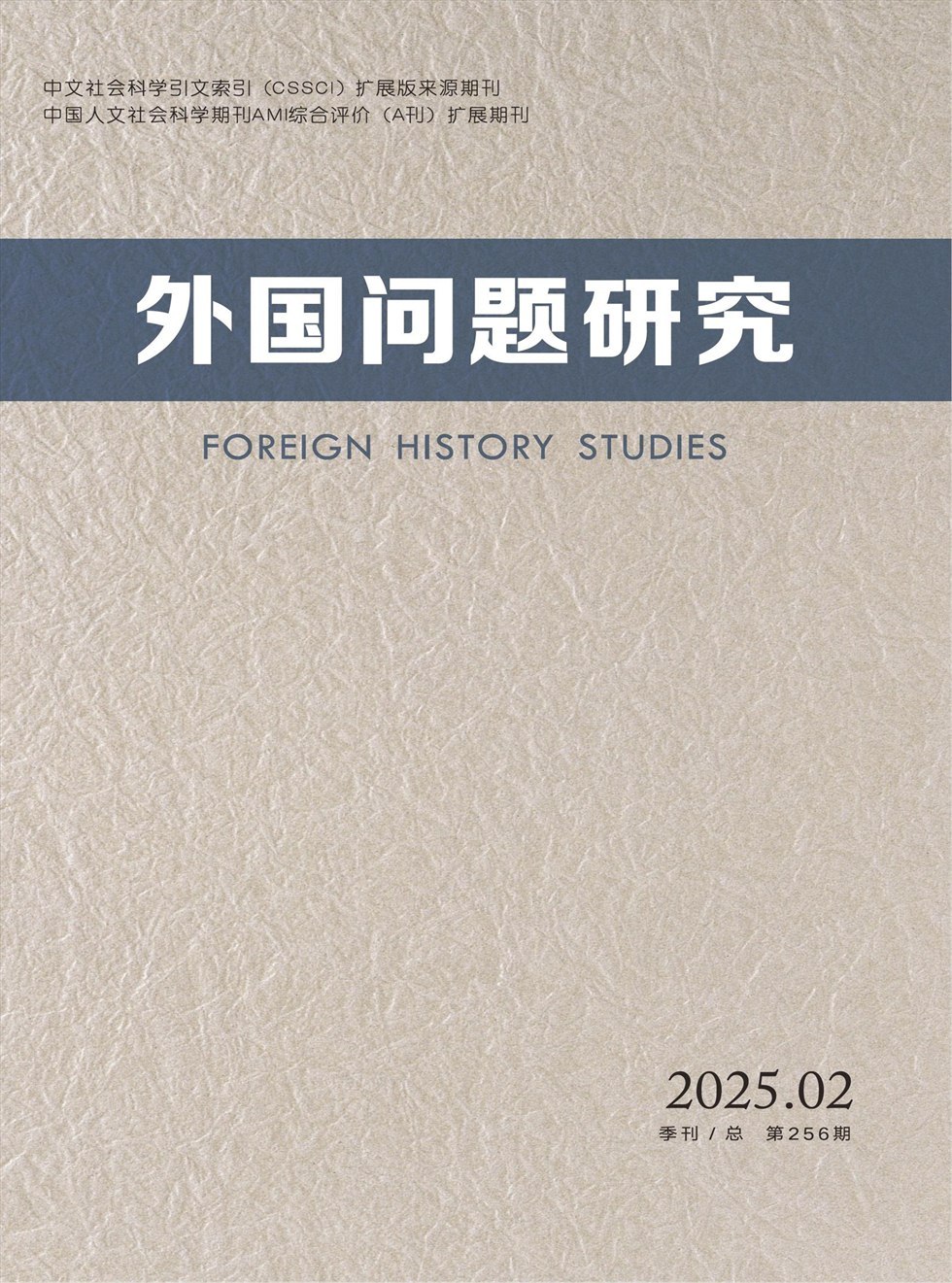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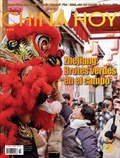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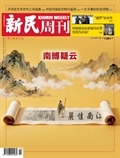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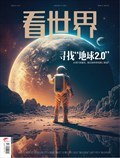



 登录
登录